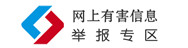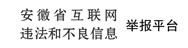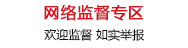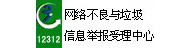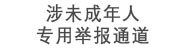邵 敏/文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系中,戏曲艺术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与精神传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戏曲艺术杰出代表的黄梅戏,承载着长江中下游区域皖鄂赣交界处人民的共同记忆,深刻体现了近代农耕文明伦理及民间智慧,已超越地域范畴,融入中华文化血脉。与此同时,黄梅戏还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融合了艺术表演、物质遗存、民俗活动及价值观念等内容。当代语境下的黄梅戏传承发展,可以激活历史记忆、维护文化多样性,实现审美共识及价值观念传递,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注入精神力量。
黄梅戏凝聚的集体记忆
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在揭示历史与记忆互动关系的记忆之场理论中,认为民族认同的建构依赖于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物质、仪式或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场域既是记忆的容器,也是历史重构的媒介。黄梅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人民的集体记忆宝库,通过代代相传的经典剧目、凝练的表演技艺和相关民俗活动,生动保存并传递了农耕时代的生活经验、伦理规范及价值追求,奠定了中华文化认同构建的历史根基。
经典剧目与民俗生活的记忆融合。黄梅戏的集体记忆功能突出表现为传统剧目对农耕社会图景的深度描绘,以及与民间生活的血肉联系。《天仙配》《女驸马》《打猪草》等代表性作品,无不植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乡土社会土壤,并在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场合被反复演绎。例如“你耕田来我织布”这一《天仙配》中的经典唱段,便是小农经济背景下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的生动展现,而七夕节演《牛郎织女》、元宵节演《夫妻观灯》则是艺术叙事与民俗展演的结合。这些可感知、可共情的传统剧目,已成为存储和传递长江中下游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集体记忆的活态载体。
艺术范式与传承谱系的身体记忆。集体记忆延续过程中,离不开言传身教和特定文化场景的维系。严凤英、王少舫等表演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确立了黄梅戏表演范式的审美标准,将表演转化为可模仿和亲身体验的身体记忆。严凤英塑造的七仙女形象、王少舫诠释的董永角色,扎根乡土,富于泥土气息,连同他们的演出档案资料、口述历史记录及弟子传承谱系等要素,共同构成了跨时代的文化符号和艺术资源库。在一代代黄梅戏人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代际学习模仿与演出实践,经典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精神被不断复制、强化,并在时间流变中鲜活延续,历久弥新。
方言声腔与地域风物的空间认同。记忆之场不仅存在于时间维度,更寄托于具体的物质载体与空间场域。黄梅戏通过方言声腔系统及地域意象体系,勾勒出长江中下游文化圈的认同边界。语言上,以地方方言为基础的咬字归韵声调系统所形成的独特音乐美感,在本土观众的听觉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成为游子寄托乡愁的重要媒介。空间上,遍布城乡的古戏台、节庆观灯风俗传统以及舞台上呈现的渔樵耕读场景和地域物产风貌等,共同编织出近代农耕文明的风情画卷。当“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的旋律响起时,被记忆激活的地理空间就转化为情感认同的文化空间。
黄梅戏与时俱进的创新
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厚重的历史积淀,更体现在持续的自我革新,通过传统元素的现代转化,成功实现与当代社会的有机融合。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自觉理论在此得到充分印证——一种文化首先要有自知之明,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才能和其他文化一起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境界。在全球化背景下,黄梅戏凭借明确的认知定位、跨领域的整合以及对时代议题的敏锐把握,完成了从地方艺术形式向国际化文化符号的转变。
从乡土艺术到文化IP的转型跃迁。黄梅戏的集体记忆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陈列,其生命力的延续,恰恰在于其传承中不断创新、与时代展开深度对话的能力。其创新转型本质上始于对自身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现代化呈现,是从地方性民俗表演向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艺术表达的自觉升华。在传承《天仙配》等经典剧目所蕴含的自由、爱情等主题的基础上,新时期的黄梅戏更注重从现代视角切入传统叙事。《徽州女人》反思封建制度下的女性生存困境,《红楼梦》以宝玉的主观感受为主线对经典进行重构,现实主义作品《公司》更是对社会百态展开了批判性呈现等。这些涵盖历史、文学与现实题材的多元作品涌现,昭示着黄梅戏在呈现形式和意蕴内涵方面的探索与突破。与此同时,在学术研究与文旅融合等多方力量和资源的加持下,黄梅戏的文化价值有了质的飞跃,成功实现了从地方剧种到具有思想深度和广泛影响力的文化IP的跨越式发展。
从传统剧场到多领域媒介融合传播。黄梅戏的创新自觉不仅停留在内容叙事层面,更体现在其突破传统舞台展示的时空限制,进行灵活多样的跨媒介尝试。20世纪中叶,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女驸马》的诞生,堪称是里程碑式的破圈传播,成功创造了“梅开一度”的辉煌,让一个地方剧种跃升为全国性的文化现象;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黄梅戏电影、电视剧大量涌现,出现了“梅开二度”的盛况,巩固了其在民众心中的艺术地位。在数字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青年群体聚集的抖音、B站等数字空间成为黄梅戏生长的新沃土。《2023抖音非遗数据报告》表明,传统戏曲中,打赏收益最高、同剧种间竞技最频繁的都是黄梅戏;更深层次的融合实践则呈现于综艺节目、动漫作品及其与电子游戏的联动等,诸如动漫版《女驸马》的制作推出和定制曲目《痴情咒》植入国风手游“诛仙”等,黄梅戏传播空间得到多维扩展。
从本土叙事到全球话语的时代回应。黄梅戏当代创新最深刻的意义体现在其艺术视野的宏大转向——从地域特色叙事升华为对人类命运共同话题的关怀,使其彻底超越了地方戏曲的文化局限。例如《遍地月光》(2017)与《老支书》(2018)聚焦基层治理现实问题,《绿水青山带笑颜》(2022)对生态文明理念进行艺术化阐释,《碧水东流》(2024)则深入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命题等。黄梅戏的自主适应,已成功地将地方性经验提炼、转化为普世性艺术语言,成为能被世界理解的符号系统,展示了传统艺术形式介入现实、思考未来的能力。其源自乡土智慧的时代回响,也是中国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表达,中华文明面向未来发展的包容特质与生命活力得到充分彰显。
黄梅戏的中华文化认同
如果说集体记忆与创新发展奠定了黄梅戏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基础,那么情感共鸣则是从认知向认同跨越的关键纽带,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恰可佐证这一观点。在皖鄂赣交界区域广泛流传的黄梅戏艺术,凭借其深入民间生活场域的文化形态、平民化的叙事以及共享的价值内核,在伦理观念、家国意识及审美表现之间架设起个体情感与共同体意识的桥梁,黄梅戏得以突破地域困囿,成为参与中华文化认同构建的重要载体。
伦理情感的民间表达与文化浸润。黄梅戏的情感根基在于其始终深植于以家庭、社群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体系,通过艺术化的呈现方式进行浸润式传播。其经典剧目很少有抽象、宏大的概念,而是将其进行民间化、生活化的转译与呈现。例如,传统剧目《荞麦记》中,通过王家对境遇不同的三对女儿、女婿态度的对比,以及女儿女婿对王家遭遇家庭变故前后态度的变化,让观众细细体味其间蕴含的贫富观念,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孝道与亲情;《慈母泪》中,也将无私的母爱具象化为逃荒路上的忍饥挨饿、深夜的纺线织布等细节,使得母爱这个抽象名词变得可触可摸;等等。将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普通人的情感选择和日常叙事,精准捕捉了人们对爱情的真挚渴望、对家庭的忠诚守护、对正义的本能追求等相通的人类情感,保证黄梅戏在不同时空能够获得认同。
家国情怀的戏剧同构与精神升华。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积极回应时代变革,成功实现了民间叙事传统与国家主流话语体系的结合,也实现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戏剧性同构。《党的女儿》《江姐》等现代剧目将革命英雄主义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注入传统戏曲;即便在《牛郎织女》这样的神话题材剧目中,“空守云房无岁月”的经典唱段,也被普遍解读为对自由解放的诉求和对封建桎梏的批判。这种结合找到了民间情感与崇高理想之间的共鸣点,个体情感遭遇升华为群体的普遍命运写照,使革命精神与主流价值观念通过亲切熟悉的艺术形式深入人心,民众对现实家园的情感依恋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被唤醒,完成了政治话语的在地化表达,家国一体的集体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得以强化。
审美形式的普适共情与文化共享。黄梅戏所特有的情感认同,不仅源于其动人的故事与价值内核,还存在于可共享的审美实践与文化经验场域之中。如安庆方言的声调韵律,源自日常生活场景的表演程式,以及贴近民间审美的服饰与音乐体系等。在“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旋律中,不同地域的观众,都能在音乐情绪与表演程式中产生情感共振——或是刻入骨髓的乡音记忆,或是超越了地域隔阂的普适性审美享受等。声、形、情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亲和力与审美愉悦,突破了语言障碍与地理阻隔,使得黄梅戏演变为非意识形态化的情感连接载体,成为人们共享的愉悦审美体验与文化记忆积淀。
从地方戏曲艺术演进为国家文化名片,黄梅戏是展示中华文化认同的独特样本。展望未来,黄梅戏的传承发展对内要深入挖掘其质朴清新的艺术精髓和中和之美的哲学内核,并利用数字技术和教育渠道,扎根当下,持续焕新;对外要勇敢走出去,让黄梅戏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文化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坚持内外兼修、古今结合,黄梅戏必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更加深沉、鲜活的文化动能。
(作者为安徽省社科普及基地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艺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